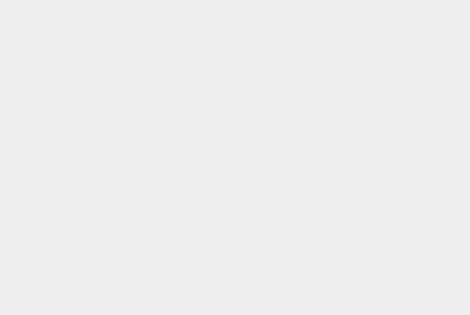戈尔巴乔夫被大多数年长的俄罗斯人所憎恨,因为他们出生的国家--苏联在他的眼皮底下解体了。他的现任继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现在正在发动一场战争,把它重新组合起来,但戈尔巴乔夫、普京和大多数其他俄罗斯人都犯了同样的类别错误。他们认为苏联是一个国家。
它并不是。它是一个帝国,从根本上说,与之前几个世纪将世界大部分地区分割开来的其他几个欧洲帝国没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与之前在5000年的 "大众 "文明中的数百个其他帝国没有什么不同。
几乎所有这些帝国的中心都有一个执政的民族或语言群体,而外围则有各种臣民。它们的规模在历史上受到非常缓慢的长途通信的限制,但远洋轮船的出现使它们在17世纪时能够走向全球。而且,归根结底,他们都是被武力统治的。
英国、法国和荷兰帝国从未将他们的帝国与自己的国家混为一谈,因为他们的殖民地与祖国隔着数千公里的海洋。俄国、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的情况则比较棘手,它们的所有属地都通过陆地相连,但后两者在1918年时已经消失。

剩下的是俄罗斯帝国,它落入布尔什维克革命者手中,并被改名为苏联。但它的边界并没有改变,只是在最西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获得了独立。
这就是俄罗斯民众的困惑的来源。因为共产党人声称自己是'反帝国主义',甚至在斯大林时代之前都不使用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陈词滥调,所以俄罗斯人很容易认为苏联都是同一个'祖国'。但主体民族注意到了。
当戈尔巴乔夫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以武力威胁作为维持帝国团结的手段时,非俄罗斯民族自然而然地把这当作一个信号,即他们可以离开。而他们的离开确实不是 "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如普京所说);它是欧洲帝国解体的最后一幕。
当然,臣民们离开了。一些殖民地人口与俄罗斯人截然不同,如中亚的穆斯林 "共和国"。有些人在外人看来很相似--例如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但他们真正的历史怨恨就像爱尔兰人和英国人之间的怨恨一样深刻和不可调和。
西伯利亚和远东留在俄国,因为那里被征服的人口是生活在小群中的原住民。早在18世纪,他们的人数就大大超过了俄罗斯定居者,他们的未来充其量就像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第一民族"。
三十年前,最后一个欧洲帝国就是这样被非殖民化的,现在试图把它重新拼凑起来,就像英国试图重新征服爱尔兰一样,是愚蠢和徒劳的。是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有很多共同的历史。是的,不了解他们的人很难将他们分开。但不,他们不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谈到的 "小差异的自恋 "吗?是的,当然是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和平而富有成效地生活在一起,就需要某种共同的身份,自从大众文明兴起以来,大量的人已经成为标准,而构建这种共同的身份是艰苦的工作。
因此,两种语言,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实际上并不比格拉斯哥英语和牙买加英语相差多少,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竖立为不同 "民族 "之间的鲜明分界线。但他们不谈宗教,因为乌克兰人在这一轴线上的分歧太大。
历史,不管是假的还是真的,也有帮助。俄罗斯人分享了一个故事,据说现在在乌克兰东部对讲俄语的人进行了种族灭绝;许多乌克兰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holomodor')是由他们的俄罗斯统治者故意造成的。
你可以希望将其带入同一身份的人只有这么多,这就是为什么非洲有52个国家,而南斯拉夫曾经是7个国家。这只是非殖民化进程的一部分,但俄罗斯人还没有掌握到这是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
Gwynne Dyer is an independent journalist whose articles are published in 45 countries.